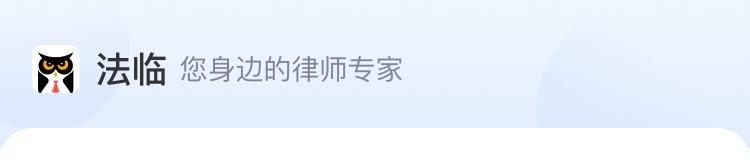

名义收款人与实际用款人,谁才是还款责任主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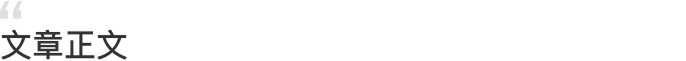

.e08ff51.png)
民间借贷中,当款项交付对象与实际用款人不一致时,如何认定借贷主体?关键在于穿透“资金通道”表象,以借贷合意和资金控制权为核心,厘清“形式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的责任边界。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相关案件。
2017年4月,孟某通过银行账户转账给高某30万元,次日高某将30万元转账给郝某。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高某通过银行转账或微信转账,每月支付给孟某3000元。2019年11月,实际用款人郝某向孟某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孟某30万元整。2020年5月,高某通过银行账户向孟某转账5万元。孟某认为,其与高某之间构成借贷关系。故孟某诉至法院,要求高某偿还剩余借款25万元。
高某辩称,账户往来记录不能证明其与孟某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自己只是作为中间人,为孟某与郝某之间的借贷行为提供了一个账户作为汇款通道。借款时,孟某将款项通过高某转给郝某;还款时,也是郝某先转给高某,再由高某代替郝某向孟某还款。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高某向孟某每月支付3000元,是代替郝某定期向孟某支付利息。高某向孟某汇款5万元,并非是还款,而是因孟某母亲生病,高某作为孟某的朋友,提供款项用于孟某母亲治疗。
此外,高某主张自己并没有向孟某出具任何形式的借款凭证,二人之间没有借款意向,不应承担还款责任。因此,应当由郝某归还孟某借款。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有三个争议焦点:
(一)借贷合意存在于孟某与高某之间,还是孟某与郝某之间?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认定借贷关系需聚焦借款交付时的真实合意。本案中,借贷合意存在于孟某与高某之间,还是孟某与郝某之间,关键在于探究30万元借款的借贷合意如何形成。
根据查明事实,孟某于2017年4月将30万元款项直接汇入高某名下的银行账户,高某随即处分资金,证明高某已实际取得并控制了该笔借款。高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收到借款后并未向孟某提出异议,构成默示借贷合意。高某将借款转给郝某的行为,则是以实际履行的方式表示与孟某之间达成借贷合意。
此外,孟某与高某系前同事关系,高某与郝某系亲戚关系,孟某在出借借款时与郝某不相识,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孟某与郝某之间存在直接借贷意思表示。
(二)高某向孟某转账的行为,应如何进行法律评价?
本案中,自2017年11月至2019年10月,高某每月向孟某支付3000元。2020年5月,高某再次向孟某转账5万元。高某连续26个月向孟某支付固定金额,符合利息特征,后续支付5万元,形成履行债务的意思表示,高某持续性还款行为构成对债务关系的确认。
此外,高某虽主张上述转账行为系“代付利息”“友情资助”,但均未提交证据证明。
(三)郝某出具借条,是否改变原始债权债务关系?
借款合同应当遵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款的实际流向不影响合同主体的确定,即借款的具体用款人及流向并不能否定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虽涉案款项于2017年4月出借后由郝某实际使用,但并不能以此否认孟某与高某之间已形成的借贷关系。
郝某向孟某出具借条时,距借款发生已逾31个月,且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孟某同意高某将债务转移给郝某。因此,涉案借条仅系郝某对高某的内部追认,对孟某不产生债务转移的效力,不改变原始借贷主体。
综上,法院判决高某向孟某支付借款25万元。判决作出后,高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经查明后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法官提示
“法律不保护权利上的沉睡者,亦不承认无明示的债务转移。”在民间借贷纠纷中,当款项接收方实际控制资金且无相反证据时,依法推定其为借贷关系主体。实际用款人未与出借人建立原始合意的,不能简单因资金使用行为对外承担责任。
为避免因“账户中转”所带来法律纠纷,特作出如下提示:
对于出借人而言,借款时要明确债务人,完善书面凭证。要求借款人签署借条,载明出借人、借款人、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利率、还款期限等信息,同时要留存好相关证据,如资金流向记录、聊天记录等,以证明借贷合意。
对于名义借款人而言,一方面要明确法律地位。若款项涉及“代转”,建议名义借款人与出借人、实际用款人之间签订书面协议,明确仅负责代转款项,不承担还款责任。同时,要求实际用款人向出借人出具借据,由出借人签署知情同意书,避免被认定为共同借款人。
另一方面要及时追偿止损。实践中长期规律还款,易被推定为债务履行,构成对借款关系的默示认可。若需先行还款,需保留向实际用款人追偿的证据,如还款凭证、追偿协议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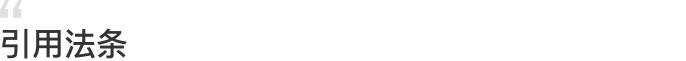



专业定位问题,针对性提供解决方案






